《煮海成聚:明清灶户与滨海社会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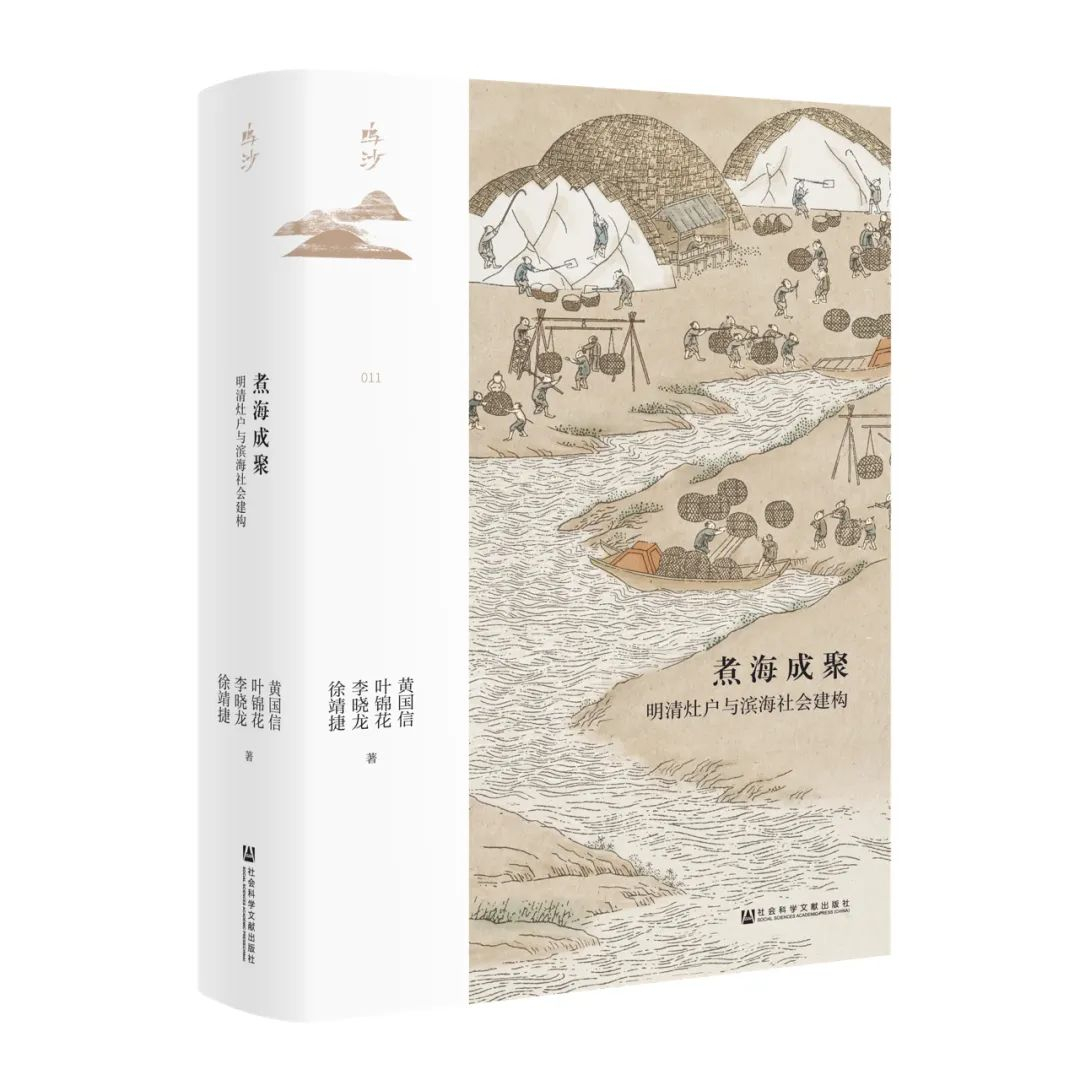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明清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着一群身份复杂的人,他们多以灶为籍、以盐为业,借此而成聚落。本书广泛利用民间文献,深入理解民众生活,揭示这一群体生活地区社会演化的基本特征和逻辑。
在明初以业为籍的基础上,伴随明中叶市场化进程加速,商业资本开始进入并逐渐主导盐场经济。与这一进程相结合,在受海水浓度变化影响的具体社会生活中,盐头、盐灶、宗族、商垣等民间自组织,为了应对朝廷课税需求,灵活运用朝廷“以籍定役”的制度设计,与王朝国家不断对话与互动,沿海的商、民、军、渔、灶等人群不断地转化着身份与户籍,慢慢产生多者合一的宗族和其他社会组织类型,“煮海成聚”,构建出明清东南盐场地区独有的社会结构。
绪论
煮海,指的是沿海灶户煎煮海水生产食盐。灶户,是滨海地区的重要人群。传统时期,在中国广阔的海岸线上,散布着众多盐场。在滨海地区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盐场的历史却并未得到足够的、与它的地位相称的关注度。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众所周知,明代人户管理“以籍为定”,灶户与“军”、“民”、“匠”并列,清代淡化了“军”与“匠”二籍的专门户籍色彩,但出于征收盐税的需要,仍保留灶户作为专门职业户。然而,迄今为止,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民籍或者军籍。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重点的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闽潮沿海以及华北平原地区的研究,广泛涉及民户的经济发展、基层组织、民间信仰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年来,军户研究也在于志嘉、邓庆平、宋怡明、杨培娜等学者努力之下,有了长足的进展,他们既注意制度规定及其实际运行,又关注地理环境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是,灶户群体和灶户社区的历史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滨海社会建构过程,并未引起学界的相应重视。既有的盐史研究,集中在制度史、财政史、商业史和技术史层面。在为数不多的灶户研究中,刘淼、纪丽真等人对江苏、山东、天津等沿海盐场地区灶户的土地租佃、赋役关系做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徐泓、王方中、佐伯富等人则重点厘清了明清时期王朝关于灶户的制度规定,并初步涉及这些规定在地方的实际运作,将灶户的生产技术、食盐的运销与私盐等问题结合起来,在盐史的层面为盐场与灶户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背景知识。但总体来说,目前对灶户群体和灶户社区所进行的整体史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灶户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史料问题。由于历史上盐在国家财政中极为重要,明清以来,大量的盐法专志和盐法档案不断生产,也不断被今天的研究者引以为据。但是,这些制度性的、官方的史料不足以支持对灶户的深入研究。因此,要突破目前灶户研究的瓶颈,就需要在资料上有所突破。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一学术难题的最重要史料,就是民间文献。其中最为关键的资料,无疑就是灶户家族的谱牒以及盐场地区的碑刻、契约。本书就是在广泛搜集民盐场灶户民间文献的基础上,对明清以来东南沿海灶户生活地区的社会史展开的综合研究。我们期望本研究重点探讨灶户的户籍赋役制度、王朝的灶户管理系统与灶户社会组织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倭乱、迁界、王朝鼎革等重大事件以及海岸线东移、人口增长、白银流入等资源环境变迁与东南沿海灶户历史过程的关系,揭示明初灶户主要归属盐场管理、民户归属州县管理,到清代基本上民灶管理合一,以及部分盐场从明代灶户的“仓埕-灶甲”系统到清代转变为“埕-团乡”系统的演变过程,研究在王朝制度的影响之下,军、民、灶不断地转化着户籍与身份,并且慢慢形成军、民、灶合一的家族结构的过程,形成明清东南沿海盐场地区社会变迁的总体图景,为学术界今后构建东南沿海包含各种人群的整体史提供基础。
本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对民间文献的重视。显然,民间文献对于深化盐场历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切了解国家典章制度如何在盐场运行,加深我们对盐场制度运作机制的认识与理解,还可以让我们把握盐场社会和滨海的整体面貌。只有在深刻掌握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可以系统而深入地理解传统时期的盐场历史和滨海区域历史。
首先,历代王朝出于控制食盐生产的目的,都会建立起一套盐场制度,并以文字形式将其书写于相关媒介上,作为盐场运作的依据。以往的盐场历史研究,主要依据这些制度条文,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盐场历史的不少解释。但这些解释,总体仍过于抽象与概括。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国家的盐场制度如何具体地在盐场运行,我们在明清时期的两淮、两浙、两广、福建盐区的一些地方展开了民间文献的收集与调查,获得大量族谱、碑刻、契约等文献,并将它们与王朝的盐场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盐场制度运行的诸多问题的了解。
灶户户籍的确定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它经过了两个步骤:一是洪武三年(1370)推行户帖法,“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二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立里甲制度,规定“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据此可知,明初官府佥定了一批民众充当灶户。但灶户如何编佥呢?汪砢玉在明中叶修《古今鹾略》,曾指出“国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产者充任”,明中后期朱廷立在修《盐政志》时,则进一步指出,淮浙盐区是佥选“丁田相应之家,编充灶户”。可见,“丁田”、“丁产”是编签灶户最为重要的原则。不过,这样的记载,只揭示出灶户编佥的原则,至于编佥的具体过程和运行细节,就需要借助民间文献来了解了。
我们发现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山场村吴姓的一份族谱,有记载道:“四世祖东塘,……因洪武定天下而后承纳税盐,是为灶户”,这说明,明初的灶户编佥,主要是跟地方人户所纳税种联系在一起的,纳何税,即佥为何户。但吴氏族谱的这一表达,仍然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判断吴东塘“承纳盐税”的由来,是从元朝继承而来?还是被新编佥而来?一般认为,朱元璋在明初整顿户籍采用的是“照籍报抄”的原则,据此,则明初的灶户应该是从元朝继承而来的。
不过,实际情形却比较复杂,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在福建石狮永宁镇沙堤村调查时,考察沙堤龚氏祠堂,发现了《沙堤龚氏族谱》,对此问题的了解有重要帮助。进入沙堤龚氏大宗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居然在他们的宗祠里,赫然摆放着一位姓蔡名守拙的人的神主牌,龚氏族众祭拜祖先时,照例要祭拜这位蔡先生。这自然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经过访谈,得知蔡守拙是龚氏的姻亲,曾经抚养过龚氏先祖,此事发生在元朝中后期。仔细研读多个版本的《龚氏族谱》则可发现沙堤龚氏二世祖早逝,其妻蔡氏亦积忧成疾而死,其子龚均锡遂由母舅蔡守拙抚养长大。在元朝的户籍体系中,龚均锡遂入灶户“蔡仲永”户籍,承担“蔡仲永”户的灶户户役。这是元朝时的情况。不过,元明之交,户籍重新整顿与登记的过程中,龚均锡的后人龚名安把蔡仲永户的户名交给了其义男蔡长仔,而龚名安的三个儿子,除次子赴京外,其它两个儿子分别另立两个灶户户籍。这就说明,明初户籍编佥的所谓“照籍报抄”,并非简单地照抄,而是有诸多整理、登记与变化。
这些户籍是与元朝从事食盐生产或者承担盐课有直接关系的人户的灶户登记,中间虽有诸多变化,但总体上仍可视为灶户户籍的继承。而实际上,明初还有一批与所谓的“照籍报抄”完全没有关系的新佥灶户。这些灶户又是如何佥来的呢?其中的一种情况是元末明初动乱之后,有人迁徙并定居到盐场附近,就被佥为灶籍。福建晋江岱阳吴氏族谱记载了其始祖佥为灶户的历史,称:“第一世观志公号肇基,生元顺帝至正丙戌年(1346) ,卒明宣宗宣德庚戌年(1430)……就牧东山埭头,牛畜蔽野,遂成居家之志,人推富焉。时海贼凭陵,不获高枕,乃卜宅于岱山。洪武三年,应诏充盐。”这是洪武间“承纳盐税”而为灶户的另一种情况,即新佥灶户。可见,明初灶户的编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继承元代的灶税,一是新佥人户承担灶税。
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性的情况是,在有些不产盐的地方,居然有人承充灶户。晋江东部沿海的陈埭,明初即不产盐,但陈埭丁氏四世祖丁仁庵却明初编佥户籍时,却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报充了灶、军、民三种户籍。不产盐却报充灶籍,自有深意所在,其目的即在于控制当地的沿海荡地资源,这是另一种新佥灶户的情况。
在两淮盐场,明代灶户来源还有一种说法,即明初朱元璋将江南一带曾经支持张士诚的富户驱赶至苏北地区,令其世代业盐。许多学者发现,今日苏北地区的居民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 “苏州阊门”。但曹树基指出指出,明代人的著作并不攀附苏州阊门,到了清代有关祖籍苏州阊门的传说已经广泛流行,致使一般的文人学士也不免随俗,阊门的传说由此更加深入人心。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明初官方记载中灶户的来源地,我们也发现真正来自江南地区的并不多。那么,为什么当地人的族谱中会有这样的自我表达呢?经过检索材料发现,目前所见最早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苏州的是灶户是王艮家族,而官方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到灶户是从江南而来的,是康熙年间编纂的《两淮盐法志》,其“风俗”篇记载:“谓灶户率多吴民,相传张士诚久抗王师,明祖怒其负固,而迁恶于其民,摈之滨海,世服熬波之役,以困辱之。”这一说法被记入盐法志中,则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灶户来源。何维凝在《中国盐书目录》中说:“此说可补正杂各史之阙。”可见,是康熙《两淮盐法志》的明确记载成为了此说最重要的依据。于是乎,“洪武赶散”的说法越来越流行,道光年间兴化县施氏族谱序中有:“吾兴氏族,苏迁为多。”我们认为,从现有的证据看,明代苏北地区的确是迁入了大量的移民,但以“洪武赶散”为理由是清代以后移民们塑造出来的“集体记忆”。由于灶籍是世袭的,清代以来,随着“洪武赶散”说获得官方的认可,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灶籍的由来,越发地强调祖先来自“苏州阊门”故事,使得他们的“灶籍”血统“准确无误”。
我们在田野中发现的一份道光二十八年的族谱,其谱序就是以苏迁来说明灶籍身份的获得,称:“具公呈,灶户朱映才、朱连元、朱元铿、朱余才、朱广武、朱学海、朱多福、朱广口、朱承寿、朱祥麟,为睦族追远,录呈谱序求印备考事。”“窃身等始祖君亮公由苏迁至丁溪场入灶籍,……复移分双垛子,等地方有年,而离范公堤六十余里,依亭近海,潮涨糜常,族谱湮失。诚恐世代久远,支派繁衍,祭礼□隆,尊卑难清,故公同集议,按照支派,重修谱序……修谱完成,有呈请地方衙(笔者注:后残缺难辨)”。该族谱序后附有“钦加同知衔泰州分司许宪”、“道光二十八年制”并加盖“泰州分司”印。这与其他族谱相比,较为罕见,因而特别珍贵。从序言中可见,朱氏族人在道光年间修谱之时,虽然声称前有族谱,但都散逸,则此次修谱乃朱氏族人第一次修谱。我们知道,清王朝对于户籍的管理远没有明王朝严格,而两淮盐场在清代中叶以后,大量的商人在这里雇佣生产,“灶籍”与“业盐”完全分离。朱氏对祖先朱君亮“由苏迁至丁溪场入灶籍”这一模糊的说法,原本是经不起考究。但是朱氏族人呈请泰州分司后,却能够得到分司同知的认可,为其加盖印章,则朱氏族人灶户的身份得以认证。这说明,朱氏族谱序言恰好体现了“苏迁”是“灶籍”获得的正当来源,这就是“苏州阊门”的传说会流行起来的原因。
王朝盐场的制度安排,如何具体运行于盐场,官方文献中没有提供细节,需要民间文献来帮助了解的例子还有许多。盐场官员的设置就是其中一例。(下略)
后记
人生总有很多奇遇。2007年,我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本以为初次招生,生源不可能理想。没想到生活却给了我很大惊喜。2008-2009年,三位本系本科优秀毕业生或直接攻博或者硕博连读,报读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正如您所料,他们就是本书的作者叶锦花、李晓龙和徐靖捷(排名以出生时间为序),他们现在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那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虽成立仅数年,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已经在乡村社会史、西南民族史等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我从硕士论文选题开始,就在中心开创者陈春声教授的引导下,从事清代广东食盐贸易的研究,博士论文则在陈春声、刘志伟教授的直接指导下,探讨了清代食盐贸易制度的实际运作及其与区域边界的关系。我虽未曾涉足盐场研究,但已经意识到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盐场中去的必要性,且形成了相关研究计划。于是,2010年,我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东南沿海盐场社会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立项。再次出乎意料,锦花、晓龙、靖捷三位,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了课题组,并将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盐场研究,当作他们博士论文的选题。锦花研究福建盐场,晓龙研究广东盐场,靖捷研究两淮盐场。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们老家就在这三个盐场所在区域。从此,他们在广州、北京、上海、南京、福州、泉州、石狮、厦门、东莞、潮州、盐城、南通等地长时间蹲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他们还爬山涉海,走村串户,被烈日暴晒过,被冷雨浇透过,被野狗咬伤过;甚至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单独在爷孙相依为命的乡村小学校长家里住宿过。当时要是知道这些细节,我肯定会吓个半死!好在总算有惊无险,他们均在预期时间内,凭着自己的坚韧和聪慧,尤其是对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极佳敏感度,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广泛好评。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大部分内容就是他们当年研究的成果。因此,您已经猜到,本书中福建盐场的相关内容为叶锦花所撰写,广东盐场的相关内容为李晓龙所撰写,两淮盐场的相关内容则为徐靖捷所撰写。我的贡献最少,只撰写了绪论和结论部分,并整合了全书。从人文学科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产权的规范要求来说,他们三位推我为第一作者,其实并不十分妥当。因此,为了做好第一作者的份内工作,后记只好由我来撰写了。
忝列第一作者,我必须感谢一大批人。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锦花、晓龙和靖捷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他们,本书的完成是根本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带动,后续才有一批优秀青年学子的加入,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盐史研究团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这个小小的研究团队,从盐的生产到盐的流通,从盐场社会到贸易组织,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历史实证维度到理论经济学维度,正在努力尝试推进明清盐史的研究。
我要感谢陈海立和任建敏,他们对本书的写作有过直接贡献。海立跟我讨论过全书框架思路,并进行过初步整合,建敏提供了本书宋代广东盐场的部分文字和图表。
我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分社郑庆寰社长和陈肖寒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郑社长诚恳地邀请我将此书交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而且效率奇高,3月底初他见到书稿,6月初即已签约,如果没有郑社长的大力支持,本书一定还是存在电脑中的书稿而已。陈肖寒老师认真细致,核对了书稿的每条史料和引文的出处,还处理了很多令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陈老师的效率同样奇高,签约后不久的8月底,我们就拿到了书稿的一校样。我们曾计划对书稿作一些修订再交稿,但由于速度太慢,竟未能来得及赶上出清校的速度。清样出来后,我承担了本系一门新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完全抽不出任何一点点时间来校对,因此,清样在我办公台上休息了足足半年,等到课程结束,它才有机会得我“青睐”。这直接拖慢了本书的出版速度。
我还要感谢参与过本书写作与出版的所有好朋友,以及在艰苦的田野岁月中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包括但不限于温春来、陈春声、刘志伟、常建华、张侃、吴滔、杨培娜、申斌、李义琼、段雪玉、黄凯凯、韩燕仪、杜丽红、卜永坚、邹迎曦、程可石、张荣生、于海根等。
最后,我要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也要感谢结项成果评审专家的鼓励。本书是基金项目“明清东南沿海灶户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2BZS083)的结项成果之一(成果的另外部分为《明清东南沿海灶户民间文献提要》和《明清东南沿海灶户资料选编》)。成果提交后,得到了五位匿名评审专家的肯定,一致给我们打了优秀,可惜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而无法当面请益,殊为遗憾。
黄国信
2022年11月30日
编辑 / 黄慧珊
初审 / 费晟老师
审核 / 安东强老师
审核发布 / 柯伟明老师

